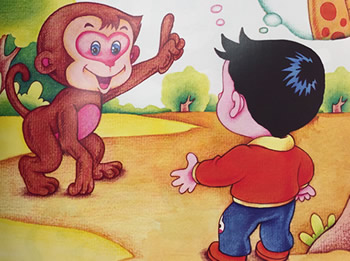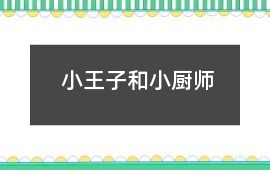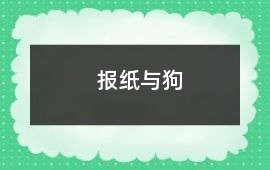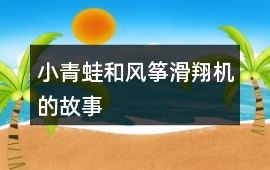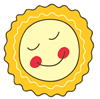睡前故事哇!一只糖皮狼
哇!一只奇怪的狼,它的皮膚是糖做的,見到它的人都想要咬一口,特別是小孩子,所以它特別特別怕小孩子,可是它偏偏遇見了愛吃糖的小寶兒。
小寶兒是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,雖然長著一張乖巧可愛的臉,可他淘起氣來簡直比惡魔還可怕,瞧他一會爬到高崗山坡一會又騎著自行車嗖嗖地在你面前飛過。直到他遇見了這條奇怪的狼,他才停下來,掏出僅有的五塊錢把糖皮狼給帶回家。
小寶兒很想舔一口,可糖皮狼說話了,它說:“哎呦呦!你可千萬別添我,我可是一條貨真價實的狼。
小寶兒一愣道:“那你不是應該在森林里嗎?”
糖皮狼說:“是的,我不知道誰把我帶到了城市,這里真是糟透了,你能發發善心讓我回家嗎?”
這讓小寶兒有些擔心,他說:“聽說森林里的狼,很可怕都會吃人的,特別是小孩,要是我把你送回森林,你吃了我該怎么辦?”
糖皮狼賭咒發誓說它絕不會吃了他,而且保證在森林里會保護他的安全。
小寶兒這才同意,他拿出自己的小書包,倒出書本裝上了一下子零食拿著糖皮狼出發了。森林的路很遠,小寶兒幾乎想要放棄了,還好有糖皮狼在邊上不住地給他鼓氣,他才堅持徒步走到了森林。
當他們走進森林里的時候,糖皮狼提醒小寶兒:“我說孩子,你可以回去了,再往前走你會有危險的。”
小寶兒同意糖皮狼的話,決定回家去,就在他轉身的時候,他遇到了一只透明的兔子。
小寶兒剛剛看見透明兔子的時候,很擔心兔子會被風吹散了,他以為這只兔子是霧氣變成的。
可這只透明的兔子卻用很輕很輕地聲音問小寶兒:“你肯定是被糖皮狼騙來的?”
小寶兒被嚇了一跳,隨后他搖著頭說:“不不不……糖皮狼它是一只好狼,它不過是求我把它送回家。”
兔子神秘地看了看周圍,接著蹦到小寶兒面前說:“我曾經和你一樣是個小孩,可是你看我現在?”
“什么什么?”小寶兒以為自己聽錯了,這只透明的兔子竟然是一個人,“你是被人施了魔法嗎?”
小寶兒想起了童話故事里的情節,壞狼、壞女巫,總是在打人類的壞主意。
“你猜對了,我是被糖皮狼施了魔法,他是這座美食森林里的老大,它統治了這里的一切,而且它經常用這種手段騙小孩子來這里,變成各種動物,供它玩耍,而你很快就會被變成一只長頸鹿的。”
小寶兒害怕了,因為他的脖子正在長長,他很快變成了一只高高的長頸鹿。他徹底被嚇壞了,嗚嗚地哭了起來,誰知她一哭森林里就下起了大雨,糖皮狼跑過了大吼:“別哭了,你會沖走森林里的一切的。”
小寶兒聽了并沒有止住哭,而且委屈地說道:“好吧!不過你要放我出去,我要回家。”
“好吧!好吧!”糖皮狼說完,小寶兒變成了一只蝸牛,它說:“現在你可以爬回家去了。”
小寶兒努力地爬呀爬,他只爬出去了一點點距離,要想爬回他的家根本是不可能的。
“糖皮狼你真是個壞家伙,你快送我回家,不然……”小寶兒變成的蝸牛大聲說道。
“哈哈!我可不怕,你這個小不點。”糖皮狼說完走掉了。
小寶兒則躲在蝸牛殼里,哭得眼淚汪汪,蝸牛殼說話了,它說:“小寶兒別哭,勇敢的孩子是不會害怕一只糖做的狼的。”
小寶兒點點頭,自信和勇氣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體里,奇跡發生了,小寶兒從新變成了人,而糖皮狼早就嚇跑了。
可它還是會回來的,因為這是它的家。
親情故事兒子!兒子!兒子!
兒子下班了,父親緊張地數著兒子的腳步聲,果然兒子“啪”地開了門,父親默默地看著他,兒子沒有看父親,似乎點了個頭,往自己臥室邊走邊脫外套。
兩人面對面準備吃飯。兒子在撬午餐肉,父親從兒子臉上看不出什么異常。
父親一字一句:“我被免職了。明天宣布。”
兒子猛地揚起臉。父親沒有在這稍縱即逝的驚訝里看到別的什么。沒有憐憫沒有安慰也沒有懊惱。兒子手不停:“你也需要休息了。”
父親感到胸悶氣短。他盯著兒子,兒子的手健美粗大,血管里青春在躍動,兒子一聲不吭。父親沒有說話也不再盯著兒子。他感到兒子匆匆擱筷,找衣服,又跨進衛生間。馬上,水聲“嘩啦嘩啦”,跟著兒子的歌聲高高揚起,聲音溫存自信,旋律跳蕩。
兒子你在想什么,你大了不再崇拜父親,你越來越沉默,你不再抱怨父親呆板僵化,不再為各種政治問題與父親爭論不休,也不再說父親剛愎自用。兒子,你甚至看不起父親。可父親這樣了你還是無動于衷嗎?這就是你這一代的冷漠理智?你匆匆吃飯洗澡是因為那打字員在等你去看歌劇?可是兒子,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需要你啊,我的官齡比你年齡還大一圈……
電視在播相聲。父親茫然四顧時才發現兒子并未出門,而是坐在他身后看書。父親不由納悶:打字員前天就訂了票,還興沖沖問他是否同去。
父親徹夜來回踱步,兒子也輾轉反側。父親老了,他的一切都老了。曾和父親這一輩很協調的背景已走向薄暮黃昏。這是變幻莫測的時代,不是僅僅需要熱血赤誠的歲月。
早上兒子起得很早,父親晨練回來,兒子已準備好早餐。音響照樣開著,而且旋律明亮歡躍。
父子倆依然沉默著洗漱用餐。兒子幾次似乎要開口,父親沉下心微顫地期待著,兒子卻什么也沒說。
父親佝僂著進臥室更衣。兒子不知什么時候站在身后捧著一套西裝。
“穿這么精神——是去開宣布會嗎?”兒子又拿過領帶走到父親跟前。父親遲疑著。
“我給你打。”兒子看著父親,溫柔的手像父親過世的妻子。父親心緊成一團。
“行嗎?”父親側側身。
父親和兒子一起看著穿衣鏡。沉默著。父親凝視兒子的眼睛,兒子也凝視著父親。兒子對著鏡子:“一夜之間你衰老許多。”兒子聲音低沉、溫柔,“可我一直為你感到驕傲,為你一輩子正直無私,一輩子對信仰的忠誠。你盡力了。”
父親心潮翻涌。肩頭上兒子的手十分有力。他感到心中的自信像空氣注入癟氣球一樣迅速飽滿地回歸。
最后接送父親的小汽車在嘀嘀呼喚,父親走到門口又折回頭:“昨晚干嘛不去找她?”
兒子沉默了一會兒,“分手了。”
“因為……我下臺?”
“大概——但這沒關系。”
兒子!兒子!兒子!
父親老淚閃爍。兒子把雙手搭在父親肩上,笑道:“結束,意味著新的開始,我很高興不再有你的耀目光環籠罩我的光彩——你說呢?”
名人故事老師!老師!
我又見著我的老師了,如朝山進香的人見到他自幼就心存感念的一位應愿之神。在今年正月的陽光里,也在正月的冬寒中,我回家奔赴我三叔的喜喪事,也去赴辦我大伯逝世三周年的莊重禮俗和紀念。在這閑空間,張老師到了我家里,坐在我家堂屋的凳子上。鄉間室內的空曠和凌亂,糾纏分隔著我與老師的距離與清寂。相向而坐,喝著白開水,削了蘋果,說了很多憶舊的傷感和喜悅,諸如三十幾年前在初中讀書時,我的學習,我的作業,我的逃課,還有我的某某同學學習甚好,卻因家庭成分偏高,是富農,似乎爺爺有所謂剝削別人的疑嫌,他便沒有資格讀高中了。自然,1977年之后的那場平地起雷的高考,他也無緣坐入考場改變自己的命運。還有另一位命運多蹇的同學,不僅在學習上刻苦,在書法上也頗具靈性天賦,人在初一時,其楷正墨字,已經可與顏帖亂真。可是后來,因著形勢家境,他不僅未再考,而且由于疾病,早早地就離開了這個荒涼熱煩的世界。
這個世界,對于有的人荒涼到寸草不生,對于有的人,卻是繁華熱鬧到天熱地燙,一舉一動都會有草木開花、果實飄香。然而對于我的老師張夢庚,卻是清寂中夾纏暖意,暖意里藏裹著刺骨的寒涼。
老師生于20世紀20年代末,讀書輟學,輟學讀書,反反復復,走在田埂與人生的夾道中,經歷了來自日本人的刀光槍影,經歷了國共征戰的循環往復,之后有了1949年的紅旗飄揚。記憶中從來都是饑餓辛勞,土改時卻忽然成了地主,這樣的命運,大凡中國人都可想見其經歷與結果的曲折變形、荒涼怪異。可是,好在他終歸識字,厚有文化。鄉村其實最為明曉文化的斤兩,雖然文化不一定能帶來尊嚴富貴,可讓孩子們認字讀書,能寫自己的姓名和粗通算術計量,也是生活所必需。于是,老師就成了老師。從一個鄉村完小到另一個鄉村完小,從一個鄉村中學到另一個鄉村中學,直至改革開放,他被調入縣里的一所高中,做了教導主任,最后主持這個學校的方方面面、角角落落的閑急高低,一晃就讓他全部人生的金貴歲月,43個春秋的草木枯榮,都在布滿塵土、青草蓬生的鄉村學校里枯榮衰落,青絲白染。
不知道老師對他的人生有何感想與感慨,他寫的一本名為《我這一生——張夢庚自傳》的簡樸小冊,讀下來讓人心酸胃澀,想到世事的強大和人的弱小,想到命運和生命如流水般在干涸的沙地上蜒蜿涓涓,奔襲掙脫,流著可謂流著,可終歸無法掙脫干涸與強大的吞沒。最后的結局是,我們畢業了,老師頭發白了;我們步入中年了,老師身體枯衰了。我們成家者成家,立業者立業,而老師卻在寂靜的人生中,望著他曾經管教、訓斥、撫疼過的那些學生,過著憶舊的生活,想著那些他依然記得,可他的學生早已忘卻的過往。
還記得初一時,他是我的班主任,又教語文。在一個酷暑天,我家棉花地里蚜蟲遍布,多得兵荒馬亂、令人恐懼,我便邀了班里十幾個要好的男同學,去幫我母親捕捉蚜蟲。自然而然,教室里那一天是空落閑置,學生寥寥,老師無法授課只能讓大家捧書閱讀。從棉花地里回校的來日上午,老師質問我為什么帶著同學逃課,我竟振振有詞地說,是帶著同學去棉花地捉了半天蚜蟲,還反問老師,地里蚜蟲遍布,我該不該去幫我母親捕捉半天蚜蟲?說蚜蟲三天內不除掉去凈,棉花就會一季枯寂無果,時間這樣急迫,我家人手不夠,我請同學們去幫忙,又有什么錯?
事情的結果,似乎我帶著同學們逃課正合了校規憲法,符合了人情事理,反讓老師在講臺上一時有些啞口無言。回憶少時的無理取鬧,強辭拙倔,也許正是自己今天在寫作中敢于生搬硬套,努力把不可能轉化為可能的開始。可是,在這次見老師時,面對這位耄耋老人,給我一生養育呵護的父輩尊者,我心里三十幾年不曾有的內疚,忽然如沙地泉水般汩汩地冒了出來。
我們就那樣坐著喝水聊天,說閑憶舊,直至夕陽西下,從我家院墻那邊傳來風吹日落的細微淡紅的聲響,老師才執意地告別離去,不無快意地說他的子女們都工作在外,孝順無比,真是天有應愿,雖然他一生坎坷,到了年老,卻子女有成,學生有成,仿佛曲折的枯藤根須,終于也繁衍出一片樹木林地。
老師從我家離去時,是我扶他起身;離開院子時,是我扶他過的門檻;送至門口看他遠去時,是我扶他過的一片不平不整的地面。我的父親離開人世太早,扶著老師的時候,我就像扶著我年邁的父親。望著村頭遠去的父親般的老師,落日中他如在大地上行走的一棵年邁的老樹,直至他在村頭漸緩地消失,我還看見他在我心里走動的身影和慢慢起落的腳步,如同寧靜里我在聽自己的心跳一樣。
說不出老師哪兒偉大,可就是覺得他偉大;說不出他哪兒不凡,可就是覺得他不凡。也許這個世界本身,是凡人才擁有真正的偉大,而偉大本身,其實正是一種被遮蔽的大庸大俗吧。